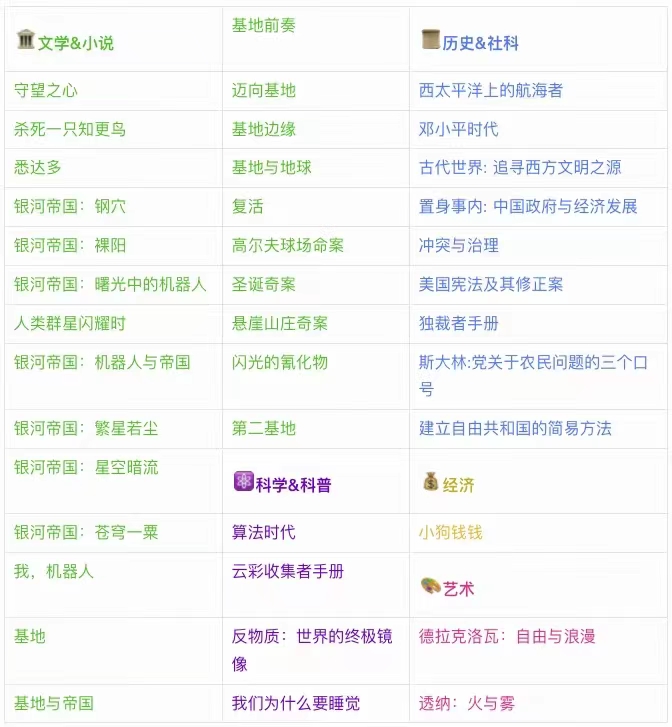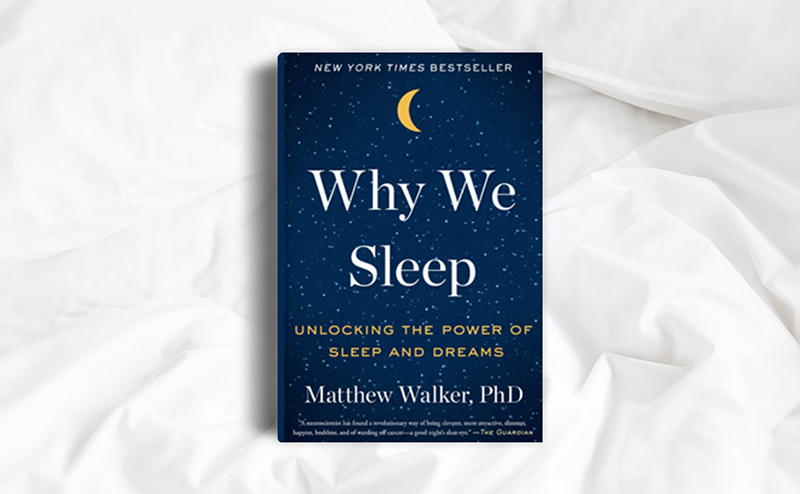旧制度与大革命
著名旅行家阿瑟扬离开巴黎是在三级会议召开后不久、攻克巴士底狱前不几天;他在巴黎刚刚看到的景象同他在外省的见闻形成对照,使他吃惊。在巴黎,一切都在沸腾;每时每刻都有一本政治小册子问世:每周甚至发行92册。他说道:即使在伦敦,我也从未见到与之相仿的出版发行运动。但在巴黎以外,他觉得一片死气沉沉;人们很少印行小册子,根本没有报纸。可是外省民情激动,一触即发,只是尚未采取行动;公民们即便有时集会,也是为了听取巴黎传来的消息。在每座城市,阿瑟.扬都询问居民们打算做什么。回答到处都一样,他说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必须看看巴黎是怎么干的。他进一步说道: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见,除非他们已经知道巴黎在想些什么。
1770年,当巴黎高等法院被撤销时,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丧失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但是在国王的意志面前,没有一个人屈服退让。不仅如此,种类不同的各法院,如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法院,虽然并未受到株连和威胁,但当国王的严厉处罚已经确定无疑时,他们情愿挺身而出,同受处罚。还有更精彩的事例:在最高法院出庭辩护的首席律师们甘愿与最高法院共命运;他们抛弃荣华富贵,宁可缄口不言,也不在被羞辱的法官面前出庭。我不知道在各自由人民的历史上还有什么比此时此刻所发生的事件更加伟大,可是这事件就发生在18世纪,发生在路易十五宫廷附近。
法国贵族阶级坚持要同其他阶级割离;贵族终于免缴大部分公共捐税,让其他阶级去承担;他们以为免于这些负担,他们就保住了他们的威严,开始时看来确实如此。但为时不久,一种看不见的内脏疾病就缠住了他们,他们日益虚弱,却无人过问;他们的豁免权越多,家境却越贫困。相反,他们如此惧怕与之为伍的资产阶级,却富裕起来,有了教养;资产阶级就生活在贵族身边,他们不需要贵族,反对贵族;贵族既不愿把资产阶级当作合伙人,也不愿把他们当同胞;贵族不久就发现资产阶级乃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过后就成其敌人,而且最终成为他们的主人。一个奇怪的政权解除了他们领导、保护、救济其附庸的责任;但与此同时,给他们保留了种种金钱权利和荣誉特权,他们估计并无损失;他们继续走在最前列,他们自己认为还在起领导作用,而且事实上,他们四周还簇拥着公证书中称作的臣民;其他的人则名为附庸、自由租地保有者、佃农。实际上,谁也不听从他们;他们是孤家寡人,当他们最终遭到攻击时,只能逃之夭夭。
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命运尽管有极大差别,有一点却彼此相同:资产者同贵族一样,最终也和人民割离。资产者根本不接近农民,避免接触农民的贫困;资产者没有与农民紧密联合,共同对普遍的不平等进行斗争,反倒试图为一己的利益创立新的不公正:贵族拼命维持特权,资产者也同样拼命谋取特殊权利。资产者本来出身农民,这些农民在他眼里不仅形同路人,而且,简直可以说宿昧平生,只有当资产者把武器交给农民时,才意识到他在无意之中已唤起了民众的激情,对此他既无力控制也无力领导;他曾经是个鼓动者,不久即将变为牺牲品。
法兰西这座大厦一度有雄踞全欧之势,当已成为废墟时,将使世世代代感到惊讶;但是注意阅读它的历史的人,并不难理解它的衰亡。我刚刚描述的几乎一切罪恶,几乎一切错误,几乎一切致命的偏见,其产生、持续、发展,实际上均当归咎于我们大多数国王一贯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
但是当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也彼此隔离,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特殊的小集团,它们彼此孤立,就像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这时可能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但其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倾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最后,只有人民仿佛从他们所有的主子的过错和失误中得到了好处,其实即使他们真正挣脱了主子的统治,他们也无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听其他们吸取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不良倾向的束缚。人们有时看到,人民在行使自由权时,竟然把奴隶的好恶也搬了过去,对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以致蛮横地对待自己的教师。
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为何大革命发生在法国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
贵族阶级层面
贵族在丧失其古老的政治权利后,已不再治理和领导居民——这种现象为任何欧洲封建国家所未见,然而他们却不仅保留而且还大大增加贵族成员个人所享有的金钱上的豁免权和利益;他们已经变成一个从属阶级,但同时仍旧是个享有特权的封闭阶级:正如我在别处说过的,他们越来越不像贵族,越来越像种姓:他们的特权显得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法国人厌恶,无怪乎法国人一看见他们心中便燃起民主的愿望,并且至今不衰。
最后,如果人们想到,这个贵族阶级从内部排除中产阶级并与之分离,对人民漠不关心,因而脱离人民,在民族中完全陷于孤立,表面上是一军统帅,其实是光杆司令,人们就会明白,贵族存在千年之后,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被推翻。
城市集中度层面
国王政府如何在废除各省的自由之后,在法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取代了所有地方权利,从而将一切事务无论巨细,都系于一身;另一方面我已说明,由于必然结果,巴黎以前只不过是首都,这时已成为国家主宰,简直可以说就是整个国家。法国这两个特殊事实足以解释为什么一次骚乱就能彻底摧毁君主制,而君主制在几个世纪中曾经受住那样猛烈的冲击,在倾覆前夕,它在那些行将推翻它的人眼中似乎还是坚不可摧的呢。
理论和行动
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
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第一种阶级的人相互之间没有丝毫先存的联系,没有互相理解的习惯,从未控制人民,因此,当旧政权一旦被摧毁,人民几乎立即变成了领导权力。人民不能亲自统治的地方,至少把他们的精神赋予政府;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考虑到人民在旧制度下的生活方式,就不难想象人民即将成为什么样子。
自由与平等
那些仔细研究过18世纪法国的人,从书本中,已能看出人民内部产生和发展了两种主要的激情,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产物,而且从未指向同一目标。
有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这种仇恨的产生和滋长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来,它就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扫清场地后,去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
另一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较浅,它促使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
从大革命开始直至今日,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这样它将反复多次,永远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被吓倒,被打败,肤浅而易逝。
在这同一时期中,对平等的酷爱始终占据着人们的内心深处,它是最先征服人心的;它与我们最珍贵的感情联在一起;前一种激情随着事件的变化,不断改变面貌,缩小、增大、加强、衰弱,而后一种激情却始终如一,永远以执著的、往往盲目的热忱专注于同一个目标,乐于为使它能得到满足的人牺牲一切,乐于为支持和讨好它的政府提供专制制度统治所需要的习惯、思想和法律。